《1 前言》
1 前言
长期以来,随着航空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用户对飞机要求的不断提高,描述飞机性能的参数和评价指标也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到 20 世纪末,人们已经把飞机的性能分为传统专业性能(如速度、高度、质量、过载等)和现代专业性能(如可靠性、维修性、保障性、生存性等)两类。对于后者,又可称为综合性能。随着军方对军用飞机要求的进一步提高,又相继提出飞机作战效能和作战适用性等参数。 20 世纪 90 年代初,美国国防部提出了“ CAIV (cost as an independent variable )思想” [1 ,2] ,即以费用作为自变量,指出效能是广义性能,费用与性能同等重要,等等。但是截至 2004 年底止,在世界航空领域尚未见从顶层高度提出用以描述顶层特性的综合性参数。笔者在长期从事军用飞机发展工程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深切地感到军方全程参与军用飞机型号发展,如何发挥主导作用,是军用飞机科学发展的关键所在。而发挥主导作用的核心问题是必须抓住涉及全系统全寿命的事关全局的飞机顶层综合特性,以统领飞机的发展。 2005 年上半年,笔者发现并提出了军用飞机效费综合特性[3] ,同年下半年在被第 25 届世界航空科学大会录用的《军用飞机生存性评估和可持续发展性综合权衡方法研究》一文中,进一步将这一综合特性称之为“可持续发展性(SD , sustainable developability)”,简称可发展性(developability)。笔者在全然不知“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概念早在 1987 年已正式提出、1992 年成为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中心议题,并被《21 世纪议程》诠释为引导人类社会健康有序走向新世纪的唯一手段[4] ,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的情况下,独立地提出了军用飞机(乃至一切产品)应当具有一种顶层综合特性,即可持续发展性,用以统领军用飞机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性与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但都是在长期实践中产生的,是对发展的一种理性认识。然而,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性又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其一,前者是针对人类社会而言,且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后者是针对军用飞机(产品)而言,揭示了军用飞机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其二,前者指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活动,后者指的是军用飞机(产品)应当具有的一种顶层属性,这种属性必须通过设计制造固化到飞机上,而在使用中充分发挥出来。如同可靠性工程、维修性工程等相继出现一样,可发展性工程的出现是军用飞机发展的必然。军用飞机可发展性工程是军方全程参与发挥主导作用、以可发展性统领军用飞机发展的一切管理和技术活动的总称,是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的一门新兴学科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2 可发展性的定义与度量》
2 可发展性的定义与度量
世界各国发展军用飞机无一不是为了增强军队的战斗力,而增强战斗力又要从本国的经济实力出发,使军事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协调,这就是军用飞机发展的本质和规律。顶层综合特性应该揭示和反映这种本质和规律。因此,笔者将军用飞机可发展性定义为“飞机在整个寿命周期内有效利用国防资源形成预期的持续战斗力的能力”。持续战斗力是一个高度综合的参数,在整个寿命周期内为形成预期的持续战斗力而合理利用所需的资源也是一个高度综合的参数,所以,可持续发展性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可以完整地表征顶层综合特性的军用飞机的固有属性。可发展性的度量导出如下:
根据定义可有
SD = CE/LCC (1)
式中 SD 为可发展性; CE 为飞机的战斗力(combat effectiveness);LCC 为飞机的寿命周期费用( life cycle cost)。
研究表明,飞机的战斗力(CE)应当由系统效能(system effectiveness,SE)和作战适用性(operational suitability,OS)共同衡量[6] ,即
CE =(SE)(OS) (2)
系统效能主要描述飞机投入外场使用时完成规定任务的能力,可表示为
SE =(A)(D)(C) (3)
式中 A 为可用性( availability );D 为可信性(dependability);C 为固有能力(capability)。
作战适用性指的是飞机投入外场使用时保持适用的程度,也就是飞机在计划的保障方案和资源下,由军用人员在外场使用时能够完成规定任务的程度。它定义为“在考虑可用性、兼容性、运输性、互用性、可靠性、战时利用率、维修性、测试性、安全性、生存性、人为因素、人力、保障性、自然环境效应和影响、文件和培训要求等因素的情况下,飞机在外场使用的满意程度”。严格地说,作战适用性和系统效能是不能完全分割的,它们有许多共同的影响因素,同时,作战适用性和系统效能又是现代军用飞机两种互为补充的使用特性。良好的作战适用性是军用飞机持久地发挥系统效能的保证。作战适用性目前尚无明确的度量参数,有人提出用适用率(utilization ,U)表示。于是有
CE =(A)(D)(C)(U) (4)
式中 A,D,C 均已有成熟的评估模型可供选用。
适用性考虑的是飞机适应现场环境(分平时训练和战时使用两种情况)的能力,目前尚无明确的度量参数,可根据各主要影响因素的定量及定性度量和评价结果,通过全面的综合判断给出结论。为简便起见,在一定时间周期内的适用率可表示为
适用率=适用次数/(适用次数+不适用次数)(5)
关于时间周期,平时训练可以年计算,战时可以战争周期(战争开始到战争结束经历的时间)计算。
对于 LCC ,可参阅文献[5] 。
将上述各式代入式(1),可得发展性的度量公式为
SD =(A)(D)(C)(U)/LCC (6)
《3 可持续发展指数》
3 可持续发展指数
由式(6)可知,可持续发展性的物理意义是单位寿命周期费用所获得的战斗力,即国防资源利用率,可以由其取值的大小判断出对国防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但研究表明,一方面由于系统效能、作战适用性、寿命周期费用等的量纲非常复杂,导致其结果既不直观又缺乏可比性;另一方面,由于系统效能、作战适用性、寿命周期费用等都与飞机性能相关,而这种相关又都是高度非线性的,在不同的取值区间内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相关关系。例如二代战机、三代战机、四代战机,它们的性能取值所处范围不同,用式(6)比较它们的优劣可能会产生误导。此外,由于国家战略从而军事战略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不同,用式(6)难以评估其优劣;而改用国防资源相对利用率,即可持续发展指数(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 , SDI)作为表征参数,可以较好地克服这些问题。
令 β 代表可持续发展指数,则
β=(CE/LCC)i /(CE/LCC)base (7)
式中(CE/LCC)i 为待评价飞机型号国防资源利用率;(CE/LCC)base 为基准飞机国防资源利用率。
将式(7)进行变换:
β=(CE/LCC)i /(CE/LCC)base =((CE)i /(CE)base )/((LCC)i /(LCC)base )=(1 +ΔM(CE))/(1 +ΔM(LCC))(8)
式中ΔM(CE )为归一化的战斗力改变量,
ΔM(CE)=((CE)i -(CE)base )/(CE)base ;
ΔM( LCC)为归一化的寿命周期费用改变量,
ΔM(LCC)=((LCC)i -(LCC)base )/(LCC)base 。
《4 综合权衡模型》
4 综合权衡模型
由式(8)可知,为使待评价飞机优于基准飞机,无论ΔM(CE),ΔM(LCC)为正或负,必有
ΔM(CE) ΔM(LCC) (9)
ΔM(LCC) (9)
式(9)即为综合权衡模型,第一象限的综合权衡图如图1所示 。
《图 1》

图 1 可发展性综合权衡图
Fig.1 Integrated tradeoff figure of developability
图中ΔM(CE)max 为归一化的在我国具体条件下战斗力最大可能达到的增加量;ΔM(CE)min 为归一化的战斗力增加量的门限值;ΔM(LCC)max 为归一化的寿命周期费用最大可能增加量;ΔM(LCC)min 为归一化的在我国具体条件下寿命周期费用至少必须增加量;ΔM(LCC)red 为考虑风险后最少必须寿命周期费用权衡空间的减缩;ΔM(CE)red 为考虑风险后最大可能达到的战斗力权衡空间的减缩。
军用飞机方案必须满足最低战斗力要求与最高费用约束,因此军用飞机的可发展性权衡是在一定的空间内进行的,不是所有高可发展性指数的方案都是可行的备选方案。首先,对于一种新研飞机,一般要求其可发展性比基准飞机要高,故可持续发展指数应大于 1 。其次,由于飞机的战斗力的提高有可能引起 LCC 急剧增加,若 LCC 超过国防经费所能负担的能力,这样的飞机方案也没有实际意义,而低于战斗力最低要求的方案也是不可取的。这样就构成了可发展性综合权衡的可行域(见图 1),只能在可行域内选择高可持续发展指数的方案。
在最佳解决方案线上的每一点,都具有最大可能达到的战斗力和消耗至少必需的国防资源的特点。
《5 示例》
5 示例
以歼 × 型飞机和歼 ×× 型飞机为算例,歼 ×× 是歼 × 飞机的一种改进型。两型飞机的效能和寿命周期费用数据如表 1 所示,寿命周期费用计算采用寿命周期小时费用。由于缺乏作战适用性的数据,本例在分析中暂未考虑其影响。
选取歼 × 为基准型号,歼 ×× 为待评估型号。由式(8)得
β=(1 +ΔM(SE))/(1+ΔM(LCC))=(1 + 2.29/5.85)/(1 + 0.843/2.307)= 1.019 (10)
计算结果表明,歼 ×× 与歼 × 相比,改型后作战能力有很大提高,但可持续发展指数仅稍大于 1 。分析其原因,虽然飞机的空战能力提高了 86.2 % ,空地作战能力提高了 79.5 % ,但由于飞机的可用度和可靠度下降,飞机的系统效能只提高了 39.1 % ,同时寿命周期费用增加了 54.6 % ,导致虽然可持续发展指数位于可行域内,但与基准型相比改进不大,表明此研制方案并非最佳方案。
《表 1》
表 1 效能和寿命周期小时费用计算值
Table 1 The values of effectiveness and life cycle costs per hour

进一步地,如果歼 ×× 能保持与歼 × 相同的可用度和可靠度水平,则歼××的系统效能可达到 9.995 ;同时,可用度和可靠度水平的提高虽然可能增加飞机的研制费,但将大大降低飞机维修费。若最终寿命周期费用略有减少,为 3.12 万元/飞行小时,则歼 ×× 的可持续发展指数为
β=(1 +ΔM(SE))/(1 +ΔM(LCC))=(1 + 4.145/5.85)/(1 + 0.813/2.307)= 1.26 (11)
由此可见,该方案飞机的可持续发展性有了较大提高,是一种较好的改型方案。
《6 结论》
6 结论
理论研究和型号工程实践表明,可发展性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为合理的军用飞机的顶层综合特性,可以统领军用飞机发展,是使军用飞机发展纳入科学发展轨道的有效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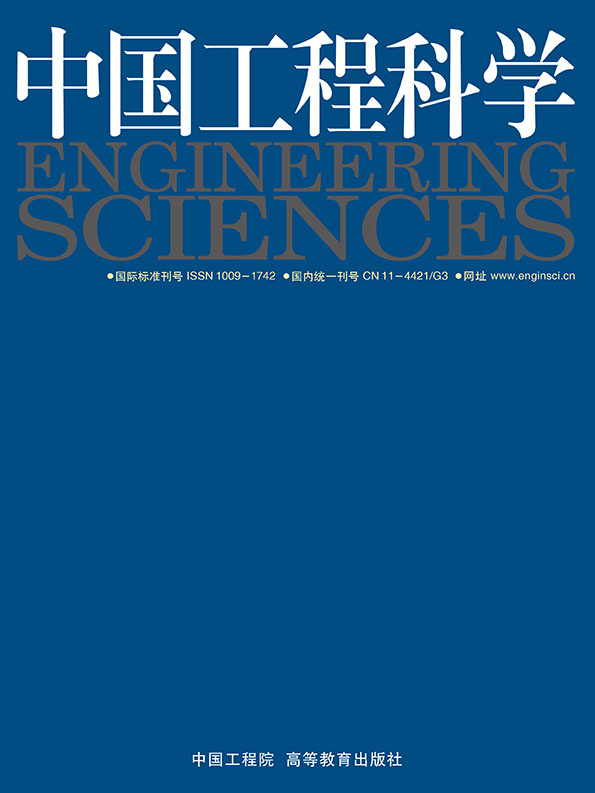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51620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5162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