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越人(约公元前407一前310年),战国末年伟大医家。司马迁通过“扁鹊者,勃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等简要描述称扁鹊即秦越人。受长桑君传授,诊病尽见“五脏症结”,犹如洞见垣外人物,只以“诊脉为名”。诊齐桓侯时因自称“寡人无疾”,以致病入骨髓。断赵简子病,仅据“血脉治也”,肯定“不出三日必愈”,果如其言。治虢太子“暴蹶而死”,使弟子针“三阳五会”,苏醒后“更熨两胁下”,调适阴阳,服汤二旬而康复如故。考秦越人与赵简子、虢太子并不同时。但从越人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时名扁鹊”,则知称为扁鹊的名医不只有秦越人一人。联系长桑君授禁方、出其怀中药而“忽然不见”及“殆非人也”似非信史。晚年来到咸阳,秦武王诊治,太医令李醯自比不如,派人将他刺杀[1],时年已97岁。基于扁鹊以论脉著称,与中医理论体系一脉相承,试就其学术问题稍作讨论。
《1 齐赵两案的寓义特征》
1 齐赵两案的寓义特征
据推算,越人大约28岁时谒见田齐桓公午(公元前384~前379年在位),说他有轻浅疾病如不治疗将会深入发展。桓公午不信。五日后见面又说病情已有发展。连续三次,依次告诉他有病在腠理,进血脉、到肠胃、入骨髓。最后一次越人一见就走。问他缘故,说病在腠理,可用汤熨治疗;进血脉,要用针砭;到肠胃,仍可使用酒醪来治,但病入骨髓就无药可医。不久,桓侯果然感觉有病,派人再召扁鹊,早已不知去向。在《韩非子·喻老》,齐桓侯作“蔡桓侯”,每次会见隔五日作“居十日”[2]。可见故事流传较广,情节出入也大。治疗采用汤熨、针砭、酒醪等法,与《内经》记载吻合。从病情层次分明和同期在中东恰好也有鼠疫看①,疑为腺鼠疫。但在病入骨髓前竟毫无症状,这是不可思议的。但有病早防早治则是中医学的优良传统。所谓“不治已病治未病”[3],服药“不可避晨夜”[4]。直到19世纪末期的鼠疫流行,仍告诫治疗不可“失之迟”[5]。鼠疫作为古老、酷烈的地方性传染病,早在疫源地内按照自然法则流行。复杂多变的症状成为它一病多名的客观基础。直到1891年前后,才因发现“鼠死而疫作”的规律而诞生第一部以鼠疫命名的中医专著《治鼠疫方》(手稿),成为《鼠疫汇编》、《鼠疫约编》等多种鼠疫专书的滥觞。“乡复一乡,年复一年”,连年发病正是鼠疫流行最显著的特点[5]。发病高峰期常于春秋季节(平均气温在15~28℃),故统称时病、时疫。1898年,在日俄争霸下的中国东北,营口、牛庄一带鼠疫暴发,北洋医学堂有位学过中医的学员,在比较《内经》等中西医籍的基础上,认为古文献中的热病伤寒疫病等与鼠疫有关。于是编成早期科普读物《鼠疫》[6]。起病急骤、发热、恶寒、头身疼痛、脉搏和呼吸加快,极度疲乏等全身症状,食欲不振、呕吐、腹痛、便秘、泄泻等消化道症状与谵妄、惊恐、惶虑不安、神志昏乱等神经系统症状在鼠疫最为普遍。各型鼠疫病程为1周左右。若渡过一周则恢复机会增多[6~8]。在鼠疫菌感染后的潜伏期内,病原菌在淋巴腺内增殖,出现淋巴腺炎肿、疼痛、周围水肿。随着细菌排放毒素与日俱增,症状也逐日加重。若病情仅限于此,即所谓轻鼠疫;若菌从淋巴腺逸出,进入血流则可累及多个脏器,如肺、脾、脑膜、肝等[9],并发败血症疫、肺疫,肝损害则有黄疸等[8]。当然,就在鼠疫染菌的同时,机体免疫应激机制同时启动,所以4天后体内即可出现抗体。故邪正消长成为预后生死的关键。
关于赵简子病不知人(昏厥或昏迷状态)已五日的病因,至今说法不一[10]。从《素问·厥论》提到“厥或令人腹满,或令人暴不知人”[3]、《热论》重症二日即有腹满,身热、谵言;三日则厥、不知人,六日死[3]。与此病情相似,显然属于急暴病症。扁鹊仅据患者脉象推断“不出三日”必愈。与《伤寒论》记载病发于阳,七日愈;(病)发于阴,六日愈,所谓太阳病“七日以上自愈”,是邪气运行六经经脉已毕的解释暗合[4]。为何“血脉治”能判断疾病预后?现代研究发现,鼠疫菌外毒素是致大鼠小鼠心脏中毒死亡的主要毒物[9],因而也是人间鼠疫出现强烈心血管症状和脉象改变的主要原因。从中毒程度、脉象状态和预后善恶正相关来看,顺理成章。因此,尽管人物生活年代存在差误,但提示有病早治则病可愈、身可活不仅符合鼠疫的防治规律,其歌颂扁鹊首创脉学,是精通各科的全科医师,批判齐桓侯骄恣、李醯忌贤害能的丑恶行径,简直是篇惩恶扬善的檄文。而对于“六不治”和信巫不信医的提示,说明寓义胜于史实,伦理先于医理。
《2 虢太子案的描述性流行病学研究》
2 虢太子案的描述性流行病学研究
《2.1 暴蹶的病情特点与“磔禳”的防疫机理》
2.1 暴蹶的病情特点与“磔禳”的防疫机理
虢太子案是全篇的核心。大意说扁鹊过虢国,见到治穰十分隆重,听说太子暴蹷而死。诊后得知邪气“动胃缠缘,中经维络”,出现“阳脉下遂,阴脉上争”,造成气闭而不通,导致“色废脉乱,形静如死状”。他断定太子未死。(按:尽管本案与赵简子病“不知人”同有昏迷、昏厥,但描述病情抽象晦涩。暴歴,歴与蹶、厥通。)于是使弟子刺三阳五会,太子苏醒后又用熨法更熨两胁下。最后调适阴阳,二旬而康复。《正义》注暴蹷引《释名》:“蹷,逆气从下蹷起上行,外及心胁也。”[1](按:王先谦《释名疏证补》“歴”作“厥”,“外及”作“入”,与《正义》引稍异。)但邪气从下上逆,乱于心胁,出现气急喘息和神志等症状则同。据《仓公传》:“蹶上为重,头痛身热,使人烦懑”[11],可知暴歴原有头痛、发热、烦心等感染和中毒症状被省略。再从“更熨”等治法来推,病情与腋腺鼠疫酷似。明清文献已有刺“头顶心百会穴”-以“刺痧”治疗酷似腺鼠疫获效良的记载[11]。在古代,蹶或厥是相当普遍而古老的流行病。在简帛医书《十一脉灸经》中,涉及踵蹶、阳厥、骭蹶等5种歷症[12]。《灵枢·经脉》除臂厥,还有肿厥、痛厥、踝厥等共7种,不乏甲笃乙死和旦占夕死等急症[13]。《内经》有关厥病的专论,《素问》、《灵枢》共有多篇。它是发病率高、变症较多的常见急性病。在《伤寒论》,当代学者仅以四肢症状和拘急(瘈疭)对其统计,涉及原文70余条,约占398条的1/6强。而神智症状(如神昏、谵语、发狂)等昏厥将近百条未计在内[14],说明厥症在《伤寒论》中同样相当普遍,或者本来就是相同的疾病过程和状态。
对于国中“治穰”,各家有不同理解[10]。其实穰是禳的假字。《说文》训“磔”,目的是为“祀毕春气”。说三月中“有大陵积尸之气,佚则厉鬼随而出行,命方相氏驱疫”[15]。又“磔牲以禳四方之神,所以毕止其灾”[15],说明磔禳与驱傩相似,都是为了驱疫。所谓“凡言磔者,开也,张也,刳其胸腹而张之”[15],意指开裂牲畜(如鸡、狗)胸腹,以祭祀鬼神,消除疫灾。(按:腺鼠疫主要以“鼠-蚤-人”的方式传播。高发于三月气温升高、蚤类繁殖的旺季。面对突然袭来的大量疫病和死亡,眼见尸体堆积如山,疑有厉鬼作祟,因而磔裂牲畜祀除凶害。不料溅出的血液恰好吸引了嗜血蚤类,使人群免于叮咬而感染疫病,客观上起到止疫除灾效果。而鼠疫中毒的中枢神经系统症状谵妄、如见鬼状,则是支持疫病流行与“厉鬼”有关的重要“理由”。)与此类似,古代“变国火”以止时病[16]。“荻室熯造”(用火烤新房)以去毒气[17]。尽管当时不知疫病与鼠、蚤有关,《鼠疫汇编》从避“地气”出发,发现居室泥地湿黑病疫多死,铺砖筑灰则免;暗室蔽风者死,居厅居楼者免[5]。蚤性喜湿,湿地多蚤。实际上避免了疫蚤反复叮咬与重复感染。反证古代疫病流行之盛。
《2.2 从厥病流行看刺灸火熏的利弊得失》
2.2 从厥病流行看刺灸火熏的利弊得失
隋唐时期正值国际鼠疫大流行的高峰期。当时全身腺鼠疫统称风毒,仅发于脚胫的股腺鼠疫称为脚气,合称“风毒脚气”。《素问》论热厥、寒厥“必起于足下”,与《灵枢》“厥气生足悗”同[13]。病因疑“数醉以入房”[3],《千金·风毒脚气》病因与此相同[18]。可能与醉卧、性活动宽衣解带易受疫蚤侵袭有关。但王注《厥论》不顾同期多数医家解,固执己见,坚持以厥、蹶训为逆气,批评世俗谬以《厥论》传注脚气著作,“广饰方论”[3]。(按:厥、蹶等字训为逆气始于初文“并”。杨树达发现“¥”在甲骨文中是倒刻的“大”字,是颠倒人形的象形字,引伸为不顺[19],说明王注自有道理。但不识时变,否定两种病名的雅俗关系。按《说文》有欮,应是瘚的本字和厥与瘚的声旁。)所谓“瘚,逆气也。从疒,从屰、欠,瘚或省疒"[15]。王筠注“屰气”为“上气疾”[20]。“欠”像张开大口出气的人形。训气不足,引伸为欠少、欠缺等[15]。因此,欮字除並以外,病态的“欠”字也有上气、喘息、气不接续,或呼吸困难、抬肩伸背、上下相引等症状,其本身就有“逆气”的意义。故颜注《急就篇》“瘚者,气从下起,上行叉心胁也”[21]。在所有英、欠组成的文字中,蹶字出现最晚。造字之初定有如《释名》、《病源》所说,因脚馗(肿)流行而病从脚起,逆上而为喘欮,类似腺鼠疫并发肺感染等情形。经过宋·林億“蹶为脚气”[18]、经《医学纲目》和《证治准绳》的引证[22],张景岳、何梦瑶等认可才重新回到晋唐的起点。这样,分析太子所患、扁鹊所诊,刺、熨所治,应是史书记录最早腺鼠疫验案,扁鹊则是中国正史所载正确诊断,以刺、熨治疗腺鼠疫的伟大医家。我国则是最早采用选择环境居处、火烤居室灭蚤和磔禳吸引蚤类、防止疫病传播的国家。
我国以刺法治疗腺鼠疫的历史非常悠久。典型的一次是1643年8月间的“疙瘩”(实为腺鼠疫)暴发,“贵贱长幼,呼病即亡”。范氏据“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群鼠数万衔尾渡江,昼夜不绝”等记载,称之为“电击性鼠疫”[23]。10月从福建来了一位行家,诊病只验看膝湾后肿起的青筋,颜色紫黑者断为预后不良,颜色发红则急刺放血立保平安。每日诊治无数[24]。王庭在燕都亲见疫病暴发:“患者胸腹稍满,生白毛如羊,日死人数千,竟不知所名······李君见之,曰:“此痧也!”挑之以针,血出,病随手愈。”[24]王氏记载成为后来羊毛痧、羊毛瘟的由来。同一次疫病而有不同症状描述和俗名,固然与鼠疫临床症状多变有关,也与各家以片面症状命名、用不同方言表述有关。综合疫情与历史背景、发病季节与症状、预后等考察,不难确认是鼠疫作祟。如几次羊毛瘟的流行时间与乾隆年间鼠疫流行时间基本重合。着眼于病情异同,杨栗山最先将痧胀与大头温、虾蟆温、瓜瓤温等腺鼠疫别名相提并论,认为与张仲景阴阳毒、吴又可杂气无异,只是“受毒有浅深,为病有轻重”[25]。而同期日本的脚气流行,“其症候全若汉唐诸家所论”[26]。治疗推介中医文献“疼痛如刺,随病即灸,火彻便瘳”的经验[26]。初病肿痛,恰值鼠疫菌在淋巴腺内增殖而致炎肿之际。采用火焠、药熨、汤烫、热敷、灸炳,当组织温度达55℃,只须持续15分钟,便可使病原菌灭活,迅速治愈疫病。尽管原理不限于此,“火彻便瘳”是可信的。与“核起而赤者”灸其核上不同[4],《金匮要略》所谓火逆与奔豚上气、吐脓、惊怖与火邪合论[27],显然由于感染途径的差异,导致病原菌在体内所处部位不同,火熏不仅难以准确灭活炎肿淋巴腺以外的全部病菌,温度的升高反而导致细菌毒素和毒性激增[28],成为火邪致病的原因。由此为熨烫火灸等加热治疗的适应症、时机选择及其疗效与毒副作用之间的联系找到了合理的答案。
《3 中医热病模式的新视野》
3 中医热病模式的新视野
《3.1 热病流行与战争环境》
3.1 热病流行与战争环境
发热是古今中外传染病最基本的共同特点。中医热病也在不同历史时期逐步形成了伤寒热病(外感或外伤)、内伤脾胃、温疫温病等三大流派与理论,对中医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回顾战国以来直到晚清将近2500年间里,其生态环境是在没有化学除虫剂和抗菌剂、冷兵器战争接连不断的自然条件下,导致鼠类猖獗,疫病流行。在中东,与秦越人同处战国时期的古希腊,戴安尼夏(Dionysius,公元前405年在位)提到“利比亚、埃及和叙利亚一个致死的感染”;罗马与迦太基战争期间双方都有鼠疫,罗马死者约3万①。张仲景生活的东汉末年三国混战、疫病流行,“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4]。《后汉书》所载大疫共十余次。陈氏比较217年大疫与欧州鼠疫“若合符节”,认为其余各次可能都属鼠疫①。6世纪的欧洲大疫,战争状态下的东罗马鼠疫致死者达居民的半数,当时同称热病[29]。尽管都有发热,但中医文献除了急病中风、伤寒发热较多着眼于淋巴腺炎肿,以恶核、风毒、脚气闻名于世。13世纪的欧洲鼠疫,因十字军征战而“黑死”盛行。金元之交的汴京百余年间多次大疫,死者居十之三四乃至过半,动辄数达百万。李杲根1232年3月元兵围困汴京,城中疫起,“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病而死者,继踵而不绝”,对于造成百万人死亡的热病,质疑是否属于外伤(伤寒),提出脾胃内伤说[30]。吴有性则根据明末延续到五六月间、多见阖门传染,医家用伤寒之法治疗乏效,认定是不同于正伤寒的温疫[31]。堪称疫病与战争相关的典型,清朝回疆战争期间,云南连续长达百余年的鼠疫流行其中仅两年未见鼠疫记录②。20世纪60年代,鼠疫因越战显著增加。越南人死于鼠疫的人数超过死于战争的美军士兵[9]。我国伍连德和美国麦克尼尔都认为研究疫史最佳莫如中国[7]。说若能以丰富的流行病学素养,仔细地研读所有现存的中国古籍,“或许有一天真能找到解答这个问题的曙光”[32],也都注意到与鼠疫流行的显著特征,即初次肆虐后便相当频繁地反复发作。
《3.2 热病症状与伤寒涵义的历史演变》
3.2 热病症状与伤寒涵义的历史演变
尽管《黄帝内经》中方药很少,但《素问·热论》在外感热病史的里程碑意义并不因此而稍减,她几乎涉及后来所有热病理论与辨治问题[3]。例如,通过自设问答发问热病病因大致相似(“皆伤寒之类”),而预后、病程却差异很大(“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间,其愈皆以十日以上”),分析了由病邪伤害程度轻重浅深以及传变方式的不同:受邪轻浅的伤于寒(即伤寒),邪气仅仅伤及肌表,所以发热虽重,一般不会死亡;邪气既伤肌表又伤腑脏的“两感于寒”重症则死亡率很高。伤寒而病经过一日巨阳(太阳)受邪、二日传阳明······六日传至厥阴,各有相应症侯,传遍三阴三阳六经,重者六日仍有少数死亡;轻症从第七日开始巨阳病衰,八日阳明病减·····直到十二日厥阴病衰而邪去病愈。由于“两感”重症属表里同病,开始二、三日就可出现昏厥,水浆不入,至六日而死。在治疗方面通常未满三日采用发汗,已满三日则用通下,成为中医热(疫)病症论述辨治最完整的理论模型。这些规律、症状、病程恰好与鼠疫吻合。张仲景“撰用素问”,以《热论》六经为基础。因此,《素问》六经成为研究仲景六经最经典的理论渊源与诠释依据。然而对《热论》不合逻辑的误读,断章取义和望文生义,成为一切外感热性病“皆属伤寒的范畴”的依据[33]。其实《内经》中的热病与伤寒并非判断从属而是表述因果,两者只是病名与病因的关系。两者的比例为52:3[34]。伤寒只是“伤于寒”的介词省略,意在说明发热是由受到寒邪伤害所致。《难经》才出现病因、病名和兼有上述两种意义的伤寒(凡8次)。而对热病,除28难提到与腺鼠疫相似的肿和热[35],58难将热病列入五种伤寒之中。从“其所苦各不同”的症状差异和四季气候变化实际出发,将《内经》的一个病因伤寒演绎为中风、伤寒、温病、热病、湿温等既可含有病因意义,但事实已经完成了向外感病症病名的过渡,也为后来温病学说的发展留下了余地。关于伤寒病名的意义及其与发热的联系,《伤寒论》1-3条原文多次提到恶风与发热汗出的关系。特别在伤寒的定义无论已发热与未发热,强调“必恶寒”者“名为伤寒”[4]。可见恶寒是必有的、第一位的症状;初期发热则是或有的、第二位的。华佗有类似见解[18]。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方言不一。葛洪认为伤寒与天行温疫只是同病异名,却遭到《小品》作者的批评。日本江户时期中医文献家丹波元简在引证《小品》时,由于删节了原文中“古今相传”以下38字,误将葛洪“伤寒雅士之辞,天行温疫是田舍间号”引来,误作《小品》之言,开张冠李戴的先例[18]。至今我国大专院校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冼维逊.鼠疫流行史(内部资料).广州:广东省卫生防疫站,1988.91
② 中国医科院流研所.中国鼠疫流行史.(内部出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749,797
医教材和有关专著,所持“广义伤寒”说解释“伤寒涵义”的,除了曲解《素问·热论》,大多承误于日本文献[36~38]。
《3.3 从伤寒热病与内伤发热看中医学的病因推理》
3.3 从伤寒热病与内伤发热看中医学的病因推理
伤寒的得名除了与病因和恶寒症状,还有与发病季节分类有关的记载。所谓冬时严寒,“触冒之者,乃为伤寒耳”;“中而即病,名曰伤寒”。强调“从霜降以后至春分以前,凡有触冒霜露,体中寒即病者,谓之伤寒也。”[4](按:寒冷为冬令主气。在邪气伤人这一主与客、施与受的相互关系上,表达都有主动与被动的状态与区别。如果触冒是以人为主,那么中风、伤寒则以邪为主。)由于疾病现象复杂多变,抽象过程角度不一,语言表达方式因之而变。与《热论》伤寒、伤于寒以人为主即“人之伤于寒也”不同,《玉机真藏论》有以邪为主,说“今风寒客于人也”,使人皮肤闭而发热,此时可用发汗治疗;或痹不仁肿痛,则用汤熨及火灸刺去之[3]。人感风寒与风寒伤人主客不同,基本意义无别。《骨空论》有“从风憎风”,以风为百病始因。所谓“风从外入,令人振寒,汗出,头痛,身重,恶寒”[3]。其实,风从外入正是从振寒、汗出等症状中推理而来,所谓“倒果求因”。这一逻辑延续到金·李杲,有关“内伤脾胃”的论据一是猜测大抵人在围城之中,饮食不节,及劳役所伤,解围之后“饱食太过,感而伤人”,为大疫的病因定调;二是见到疫病中毒症状如口不知五谷味、极度疲劳等,于是按照“伤于某则恶某”的公式推理说道:“伤食恶食,伤食明矣!”[30]这种病因推理的局限,很快被暴发过后民间仍有大量散发“燥热”案例所否定。不久他发现有许多发热、痰结、咳嗽,遂至嗽血痰涎逆涌而死甚多。范氏以此引类作为鼠疫例证[22]。与当年暴发相比,既无围城情景,似与饥饱劳役无关。作为疫病中毒症状的发热与恶寒,在中西医书中有不同的描述的次序。由于中医只凭患者主诉和医生触摸,西医诊断则必试体温,因此,传统中医认为寒邪在表,故必恶寒;尔后化热入里,故发热汗出或但觉恶热。这样,客观的发热与恶寒症状记录在文字,则有恶寒先于发热,伤寒与热病并称的情形,成为数千年来中医描述鼠疫最显著的特点。直到明末吴有性仍说疫病初起“先憎寒而后发热,日后但热而无憎寒”[31]。《鼠疫汇编》的提法与伤寒定义相似,意义相反,说无论之前寒热如何,但“既热之后即不恶寒”[4]。可见病因推理和疾病过程的抽象只是具体真实的折射。
《4 热病病程抽象的复杂性反思》
4 热病病程抽象的复杂性反思
《4.1 热病外感、内伤的症状比较》
4.1 热病外感、内伤的症状比较
热病分为外感与内伤,尽管分析得头头是道,但除了流行特征惊人相似,李东垣、吴又可都从不同角度与伤寒进行比较,除了异口同声肯定自己所见病症与伤寒大异,同时又都说两者存在许多相似与相同。如李氏肯定发热的普遍性,说“百病俱有身热”,而且起之初两者“微有相似”、甚至与(伤寒)“阳明中热白虎汤证颇相似”,区别只在必待“一二日”后,症状才有显著变化,至此诊断才“不至错误”[30]。这就是内伤与伤寒的“始同终异”论。(按:初病一二日加上再必待一二日,与《热论》三日前属三阳,三日后转三阴近似。犹如“六日死”有“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间”的约略提法。)《温疫论》则恰好相反,说时疫与伤寒有霄壤之别,所同只是两者“皆能传胃”,届时都可用承气汤辈导邪外出[31]。所谓“传胃”,实指便秘之类消化道症状。两人一前一后,异同恰好相反。此外,热病、伤寒三日都属少阳,病位半表半里;《温疫论》三日“邪在膜原”,,同是“半表半里”,名异而实同[31]。自《扁鹊传》有“动胃缠缘”,《热论》和《伤寒论》二日都属阳明(胃),四日都在太阴(脾)。所谓“实则阳明,虚则太阴”,无非与发热、便秘、溏泄等症有关。除此,仲景还早把“呕逆”写进伤寒定义,说明他对脾胃的重视[4]。联系东垣分析外伤与内伤发热的机理:外伤发热邪在肌表,郁而发热;内伤发热,气虚下陷,乘于肾肝,其“躁热发于肾间”,是“痿厥气逆之渐”[30]。(按:痿厥气逆与腺鼠疫、风毒脚气酷似,无疑又贴近于扁鹊所论暴厥。而与伤寒、热病、两感症的热与厥同见十分相似。在《温疫论》中,发热与脉厥、体厥都有专论[31],而二厥在《鼠疫汇编》还是评定鼠疫轻、重、危候的主要依据[4]。)因此,分析内、外伤与温疫都有寒热、消化系统和神志症状来看,正与鼠疫临床特点不悖。这一规律的揭示,不仅为传统热病学说一源三流,并从现代流行病学的视野揭示中医学的历史贡献与伟大成就,为中西医结合寻找到更多聚焦点发现了新路。
《4.2 三阴三阳渊源的临床医学诠释》
4.2 三阴三阳渊源的临床医学诠释
远在《热论》六经传受以前,简帛医书《阴脉死候》已有“凡三阴,地气也,死脉也”,余类推[12]。顾名思义,阴脉阳脉不离经脉病候死症。余如《脉书·六痛》:六痛者皆存于身而不早治(“而莫智治”)将会变症迭起,就要听到死人吊哭声(“且闻哭音”)了[12]。疼痛六日便死人,与《热论》热病“六日死”,阴阳毒“七日不可治”、时毒所谓“五、七日间乃能杀人”雷同。以三阴三阳6日为标志,正可与复杂性思维路径依赖相比拟。仲景以后,巢元方将伤寒、时气、温热、疫疠,无不按一日候至六日候逐一罗列,成为疫病过程与状态结合的范式。随着鼠疫受到控制而日益少见,教材凡热病1~6日传变的“日程”,都无不认为与“具体日数”无关[39]。探讨六经问题自20世纪30年代恽铁樵氏感叹无人识得真义。经过60余年的努力,人们总结了41种解释[36],仍难免数典忘祖和瞎子摸象。偏偏遗忘了“六经传受”始于《热论》,与病程或过程论有关。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却成了老大难。源头仍在忽略经典原文解读,迷信、盲从日本或留日归来的权威。《素问·热论》与《伤寒论》的渊源本是同一理论体系的不同模型。不同版本之间有同有异,有继承也有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见仁见智也毫不奇怪。但过分强调差异,无异于否定仲景“撰用《素问》”,遗憾的是此风至今不绝。其次,妄称原文“无六经字面”更是言过其实[36]。难道“三阳经络皆受其病”[3]、“行其经尽”、“使经不传”等都离开经字“字面”了吗[4]?将具体的疾病病程三日、六日融入热病病因,将六日过归于“经络受病”抽象成为六经传变,是中医理论象数特征的又一体现,也是它与现代医学有别、所以难解难读的根本原因。现代经络研究仅用“走行线”、“管道系统”、“感传现象”等理解经络,其片面性和经络实验所以难以进行合理的科研设计、并在实验中得到重复的原因正在于此[40],也是中医学名词多义性与不确定性的生动例证。《内经》中三阴三阳的意义至少与运气、经络名称、气血多少等有关,其中有多篇与开、合、枢相提并论。近年成为诠释《伤寒论》六经的新说辞[38]。从奇邪离经,“五藏六府,折关败枢,开阖而走,阴阳大失,不可复收”等文字分析[13],主要是以战事攻守暗喻机体防御机能,似与六日病程有较大出入。因此,脱离了原始文献的探求,形形色色的六经新解还会层出不穷。开口千言,离题万里就不可避免。读者应有自己的思考与判断。
《4.3 医易先后及其历史进程的文化映射》
4.3 医易先后及其历史进程的文化映射
近期,医与易的关系因杨振宁先生一席谈而达高潮[41]。尽管中医理论思维方式的核心与中国传统文化、古代哲学的“象数”相一致,是基于经验的思辨,但就历史与逻辑的观点而论,由于人兽共患疫病的病原体先于人类社会以前的动物世界,远古就在自然疫源地存在。从考古学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已有打制的“尖状器”,新石器时代出现磨制的、可用以刺病的骨针、砭石、镵石,远在相传伏牺制九针与冶金术发明之前。无独有偶,文字史上的“医”字与“藏矢器”刺病有关[15],且有文物、文字、文献与简帛医书、《黄帝内经》和《史记》的记载和传说相参证。《内经》收有刺热、刺疟、刺痛和论述刺法治病的专论达十余篇。从文化考证,即使按照《系辞》包牺氏始作八卦、从结绳而治到后世易以书契文字[16],据“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作易者其有忧思乎”[16]的推测,到“文王拘而演周易”[1]的假说,充其量不过上下五千年。与始于距今一万年前后的新旧石器时代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再从“象数”和“路径依赖”的相关性看,尽管人类生来手足就有五指(趾),但五行见于《洪範·周书》,大约比《尚书·大禹谟》出现六府(后来演化为六律)晚了将近千年[16]。三为六之半,除了日月星三光垂象、上中下三位高下相较,难免蕴涵疫病过程三日由微而甚,由阳转阴,至六日而死的恐怖阴影。相信起病1,3,6等日数可能是古人类与疾病斗争中最早发现的日数字规律。《周易》“七日来复”[16]虽有多种解释,但恰巧与鼠疫渡过七日则恢复机会激增不谋而合。无论从感恩庆幸不死,还是相信神灵庇佑,不言而喻,刚刚走出蒙昧状态的古人类不可能会有诸如“生物钟”、“月亮单位”等精深的科学理论。《伤寒论》“七日自愈”,除了“临床经验”不宜将古人拔高或现代化。因此与任何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解释相比,疾病流行的死生之验,丧亲之痛及其日程规律留下的印象与记忆其深刻程度应是任何其他事件望尘莫及的。到《老子》提出“道生一”至“三生万物”标志着象数法则的成熟[42],三、六无疑是应用最早的道与数。与疫病中毒症状所致幻觉,不仅为相信鬼神与巫、原始宗教的七日礼拜找到了合理的解释,疫病对古人类早期行为、思想文化、人文科学的深远影响也为医早于易提供了依据。古代通过观象、数算、运筹创立了精准的历法,成为验证“天人相应”整体观的基础,而中医则通过藏象类推,意识目察,经过不断的实践、经验与修正,创造了“能合脉色,可以万全”的诊疗奇迹[3]。“万全”,无异于“零死亡”。明确了医源于疫,《易经》作为古代抽象思维的代表,同样融汇了人类与疫病斗争的经验与教训。那么,中医学的发展应当取道综合的现代科学还是依从易经与古典哲学抑或人文文化,难道还要分说?!
中医科学性与复杂性的讨论因经络实验一无所获而旧话重提。其实,她的跨学科属性毋用置疑。不能因为它难以采用严密的数理逻辑和在实验室里精确地定量分析而否认它应用性科学、复杂性科学和描述性科学的属性,犹如文史地理并不因为各有适合本学科的研究方法而排除在科学大家庭之外那样,人们未曾因此怀疑它们的科学性。笔者采用描述性方法研究中医是从解读脾虚、阴火、甘温除热开始的。这个20世纪60年代由全国10余位名老中医在《中医杂志》经过17篇论文历时3年的讨论并无结果,“七五”期间又以“脾虚症候发生机理的研究”立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当以动物实验为主陷于南辕北辙和捉襟见肘的困境之后,我们从李东垣脾胃学说与“汴京大疫”的联系确认大疫与鼠疫有关,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分析方法终于发现了脾虚症候发生机理与鼠疫中毒症状有关,揭开了李杲脾胃学说之谜[42]。与耗费国家巨资的经络研究情形相似,之前既有金凤汉弄虚作假的前车之鉴,又是名老学者(如承淡安)的肺腑之言,在既不知中医经络为何物的情况下盲目立项[43],一无所获并不意外。套用现代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研究诸如脾虚、经络之类中医理论课题,本身是对中医文献文本的误读及其研究命题的不解。如果事先把原始文献及其理论的形成过程稍加重温,或以1%~5%的经费支持立论新颖的理论文献课题,必不至于陷入如此盲目的困境。
《5 中医科学性及其传承与中西医学互补》
5 中医科学性及其传承与中西医学互补
《5.1 中医病名现代化的教训与启示》
5.1 中医病名现代化的教训与启示
名不正则言不顺,病名的意义毋庸置疑。由于历史的原因,中西医混用同一病名、指鹿为马现象十分严重,大多与日本有关。日本向来沿用中医病名与汉字。后来引进荷兰、德国西医,翻译时就错用了大量中医病名。如伤寒、霍乱、脚气等无不如此。特别是在1896年把刚刚发现的beriberi译为日文“脚気”,与我国晋唐文献“风毒脚气”相混淆。后来有西医从日本留学回来,把他们西化的中医病名带回来,成为今天医书中西病名辕北辙的滥觞。至今谬误依然屡见不鲜[45,46]。余云岫是以西医理论“疏义”中国古代疾病拓荒者,他对“痹”的解释有代表性。费尽心力释为“神经炎”和“风湿痛”(Rheumatism),连自己都觉得不可靠[47]。以扁鹊为“耳目痹医”,勉强可通[1]。但联系《归藏》:“痿痹,暴厉之疾也”则多有不合[48],而与《内经》所谓“病痹气暴发”相似[13]。由于对中医病名的复杂性、多义性、随机性及其西医病名的确定性并无研究,除收集的较多资料,这些美其名曰“科学化”的疏证由于方法不科学,结论可想而知。同时,我们自己都说不清楚的医史病史正影响着国际传播与交流。如有人讽刺我国“知名的教师及国家机构中的研究人员”通过道听途说间接地“了解经典著作”,挖苦中医授课“以假货骗人”。从上文看也许闻者足戒。但诬称我们“总是炫耀回忆过去的伟大”,根本不信中医古医籍中有疫、疬、瘟、毒······等记载,不知也不信中医长于治疗急性烈性传染病[49]。除了反映我们工作不到位,也反映其浅薄与无知。《扁鹊传》的解读回敬了“五十步笑百步”的怪论。现在报章滥用古代病名的例子屡见不鲜。如李氏批评乱用“大头瘟”,认为应即腺鼠疫[50]。中风历节、魁羸、奔豚气等特定病名,在鼠疫少见的今天依然活跃在报刊与论文[51],原因就在教材、教师“以其昏昏”[51~53]。诞生于疫病流行、经过数千年亿万次诊治疫病考验的知识体系,能否免于废弃和湮没?科教兴国,中医高等教育从无到有形成如此规模成就是主要的。但旁观者清,可以说存在严重的缺憾。特别是在教育方略、课程设置到教材内容,有许多是在理论上不合逻辑、实践中用不上,重复、空谈与谬误较多。从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对仲景学说研究的反思刚刚开始[36]。中医发展亟需继承、创新并提高。尽管课程设置愈分愈细,距离中医学理论的发生、发展过程和多模型特点已愈来愈远。《伤寒论》与《金匮》都是医圣同部著作(同一模型);《伤寒论》与《温病学》则是同类热病的不同模型。后者简明直观,甚至如鼠疫论著那样代表时代新进展的划时代成就,教材、专著或轻描淡写或全都遗漏了。这些事关中医命运和未来的教材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在信息时代和网络世界,应当借鉴探索复杂系统的新思路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54],设立总体设计部,以社会思维、用集体智慧来解决。
《5.2 坚定不移地走中西医学互补的道路》
5.2 坚定不移地走中西医学互补的道路
人为的厚古薄今,致使中医学不能与时俱进,徒然增加了学习的难度。其实,若能掌握理法方药后早期实践,精熟一个模型兼采众长便能成为一代名家。当今中医在国际上受到空前关注和重视的同时,在国内也以惊人的速度边缘化,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主要因流行病得到控制以后市场日趋狭小,也有自身学术特点的局限。中医强调实践与经验,造诣多需大器晚成。即使诊断无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三因制宜,具体分析较多,抽象的悟性与个体特点较多,也为主观随意性开了绿灯。西医是公理的,理化诊断客观直观,只要诊断正确,治法几乎大同小异。中医西医互有短长。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与使命。如何在大卫生的旗帜下加强团结协作,为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攀登高峰作出贡献?李世輝先生科技自主创新与中西文化互补的话题很有启发[55]。中医、中西医结合应当瞄准前沿,问鼎急、重、难病,面向世界与未来。近期,笔者在扁鹊治虢太子案的启示下,采用针药并举治疗多例心脑血管病,其中两个典型案例值得一提。一例因心梗数小时后行支架植入术,术中因心搏骤停达20余分钟后处于深昏迷(植物人)状态,重症监护下三月无进展。经采用针刺、醒脑开窍之剂而获显效。可惜患者发病到支架植入间的5个小时内,护理人员只是服用血管扩张药和静卧,不了解针刺对解除冠脉血管痉挛、改善和防止心梗心肌坏死有效率可达89.2%[56],竟未一试针刺,酿成终身憾事。另一例则幸运得多,患者于2005年5月19日上午自己步行入院,入院后病情迅速恶化。由躁狂而昏迷,后经头颅CT平扫,印象为:双侧脑白质脱髓鞘改变。5月23日查MRI,印象:双侧基底节及放射区缺血性脱髓鞘,左侧椎动脉变细。所幸5月20日19时及时针刺,数分钟后即趋安定,为减轻脑缺氧,防止脑损伤赢得了时间。经针药结合治疗一周后从昏迷中醒来,避免了又一起植物人状态发生。
《6 结语》
6 结语
从流行病中找出第一杀手鼠疫,为论证中医药学宝库提供了论据。自然,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余的问也就迎刃而解。人类对热病的认识跨越了漫长的时空,在西医传入前的岁月中,中医独自走过了曲折的发展道路,积累了丰富经验。防治“非典”的经验再次考验和验证了古老的中医学。当新老瘟疫袭来之初,如何从第一例险象或死亡病例吸取教训,获取来者不善的信息以便早作准备,力求把死亡率降到最低,实现古人所谓“可以万全”;与感染性疾病有关的难题,无论感染性中毒、感染性休克、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和脏器功能衰竭,在古代名医和他们的著作也许可以找到成法,如何取其精华,扬长避短,在抢救危重病例中通力合作,才是当前面临的新课题。更要在疫病重来之前着手培养、造就一支训练有素的新军,继承古老中医传统,保障无辜患者免遭厄运,依靠有效的组织领导和科学决策,实行制度创新,并用立法的形式将作为常规固定下来。相信中医急则治标,缓则治其本,救人留人以治病的方针有利于那些一时还原因不明的病症。千百年来的疫病流行与应对,实践出真知。今天,分别隶属东西方文明的两种理论和科技体系的中西医学能否找到聚焦点并走到一起,多年来笔者在由钱学森院士倡导的系统论讨论班和北京大学自然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走近复杂性探索,为打开这扇大门准备了条件,也许能为证明中医与现代科学的沟通找到通路,中医教育和科研正展现无限美好的未来。
致谢:北京大学李醒尘教授、上海原复旦大学曹树基教授、李玉尚博士、李文波、潘岩铭副研究员、吕亚芳先生、台湾李建民博士、成都任玉兰同志等为本文提供部分珍贵资料;严健民、陈业兴主任、程凯博士等阅读初稿;冯国瑞教授提出修改建议;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前所长余瀛鳌教授、中国中医研究院程華农院士审阅全文,特志谢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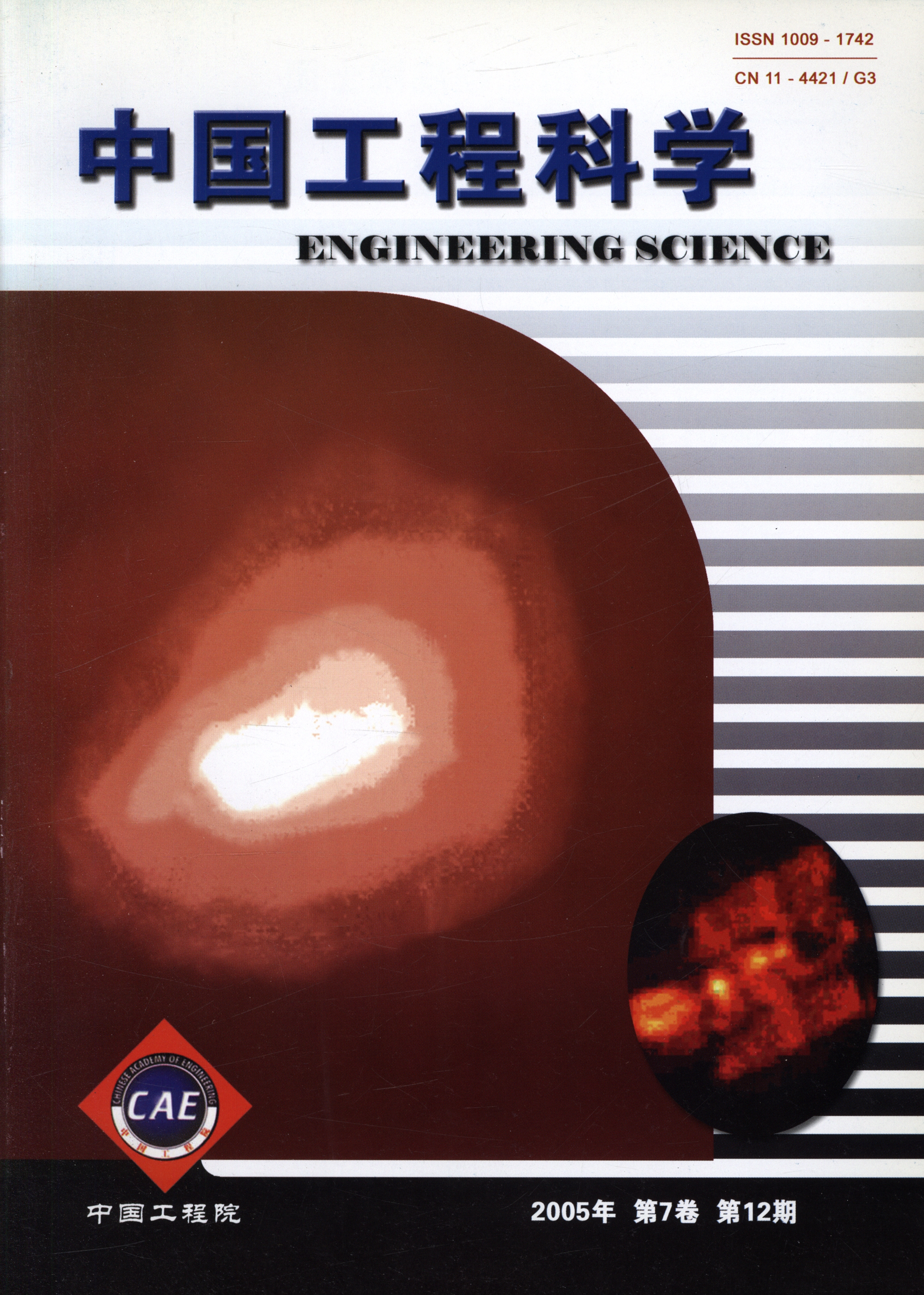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51620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5162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