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正处于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之外的另一场大流行之中,虽然它不像病毒大流行那样迅速传播,但它是潜伏的,从长远来看可能构成更大的威胁。抗微生物药物的大规模使用,推动了微生物耐药性(AMR)的出现,这些耐药微生物的数量和流行度都在增加,威胁着我们治疗常见感染的能力,减少了我们使用化疗和手术等其他拯救生命的治疗方法的机会。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2019年细菌性AMR与近500万人的死亡有关,其中约130万人的死亡直接归因于耐药性[1]。这些数字可能还会增加。
在人类医学中,抗微生物药物用于治疗感染和预防感染。它们也被用于农业,包括反应性和预防性的,以及作为动物饲料中的促生长剂。为了有效应对微生物耐药性大流行,我们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在农业中使用抗微生物药物对AMR的总体影响和对人类AMR感染的具体影响有多大?下面一些可能回答这个问题的知识是没有争议的:
(1)在动物或人类中使用抗微生物药物会产生选择性压力,导致暴露于抗微生物药物的细菌(病原体和共生菌)产生耐药性。
(2)抗微生物药物在农场动物中的使用处于非常高的水平(据估计,2017年全球在食用动物中使用的抗微生物药物超过93 000 t [2],占全球抗微生物药物产量的70%以上)。
(3)同一种细菌感染或定殖在人类和农场动物中;因此,这些物种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在人与动物之间交换。
有了这些知识,我们可以预期AMR细菌会在农场动物中被筛选出来;此外,这些细菌的后代可能会在某个时候在人类中引起疾病,或者耐药元件可能会转移到人类病原体。然而,尚不清楚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率、速度以及对人类的影响程度。
目前的证据是什么?很明显,AMR决定因素从食用动物传播到人类的速度非常快。例如,在中国,2013年从分离自猪的大肠杆菌(E. coli)中首次发现了编码抗黏菌素(mcr-1)的可移动DNA片段[3]。不到5年后,基因组数据显示,在全球范围内分离自人类和动物的至少6个不同细菌属中发现了该基因[4]。对该数据的系统发育分析表明,该基因携带的可移动DNA元件在2006年有一个最后的共同祖先[4],表明从其首次出现到其在人类中的全球分布的时间不到10年。
也有证据表明人类和动物之间共享AMR细菌。例如,一项利用基因组学分析美国同一城市的零售肉类和人类尿路感染中肺炎克雷伯氏菌的研究发现,从人类感染和零售肉类中都发现了共享序列类型[ST,由多位点序列分型(MLST)定义]的密切相关菌株的证据。作者认为,这一发现表明这些菌株最近发生了转移[5]。对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CC398谱系的分析表明,该祖先菌株对甲氧西林敏感,并在人群中传播;然而,耐甲氧西林耐药决定因素是在动物体内循环过程中获得的,这种耐药菌株随后转移到人类体内[6]。后来的工作表明,尽管确实发生了人类到动物的传播,但动物到人的耐药菌株传播更为频繁[7]。最后一个例子是,使用一种被称为脉冲场凝胶电泳(PFGE)的低分辨率分型过程来分析从坦桑尼亚附近的牛和人分离的大肠杆菌之间的关系,并表明牛、人和环境之间的转移在该系统中很常见[8]。
与这些发现相比,其他研究发现,人类与动物之间交换AMR和AMR决定因素的证据更加有限。例如,苏格兰一项对人类和动物的一个鼠伤寒沙门氏菌谱系(DT104)的20多年的研究表明,该谱系主要在两个群体中独立传播,只有有限的证据表明存在双向传播[9]。一项在英格兰西南部对耐头孢菌素大肠杆菌的研究发现,从农场动物和人类尿路感染中分离的样本之间没有重叠[10],一项对英格兰东部农场和零售肉类中的大肠杆菌的平行研究发现,这些样本与当地医院血流感染中的大肠杆菌之间同样缺乏重叠[11]。最近对意大利北部的人类、动物和环境中的15种不同克雷伯氏菌进行的一项非常大的研究得出结论,尽管有一些偶尔传播的证据,但“来自我们样本中的多种非人类(动物和环境)来源的直接传播占医院疾病的不到1%,绝大多数临床病例来自其他人”[12]。
我们如何调和这些不同的结论?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是正在研究的微生物的传播途径和转移率:导致食物中毒的微生物,如弯曲杆菌,更有可能直接传播到人类群体中,并在食源性疾病的情况下导致细菌耐药[13],尽管尚不清楚这些微生物或其耐药性决定因素将在人类群体中停留多长时间。然而,在人类和动物中更频繁发现的作为共生体的微生物(如大肠杆菌)可能很少在它们之间传播,而且传播链更长、更间接,尽管耐药细菌更有可能在到达人类群体前定殖在动物中。第二个方面是分型技术的分辨率:低分辨率技术(如PFGE或MLST)下识别的明显相似性更有可能在高分辨率技术(如全基因组测序)下消失。一项对截至2016年已发表的动物-人类AMR传播证据的系统分析得出结论:“尽管一些研究建议提供证据证明AMR可能从食用动物传播到人类,但由于研究方法的限制,无法得出关于传播方向性的可靠结论”[14],许多问题是由于所使用的分型技术的分辨率造成的。最后,必须考虑抽样框架:深度或广度不够的抽样可能会漏掉真正存在的环节;相反,密集的本地采样可能会过度强调短期或本地传播,而这些传播几乎没有更广泛或长期的影响。
最后,我们如何了解更多,为什么我们需要了解?未来的研究必须使用高分辨率技术,如全基因组测序,并且必须建立在广泛和适当的抽样框架上,包括基于人类和动物的抽样框架。理想情况下,这些方法应该包括纵向的、地理范围广泛的、系统的和无偏倚的监测方法。他们必须考虑到所研究的微生物的不同生态位,并认识到不同的微生物(和AMR决定因素)将以不同的方式表现,而且对单个微生物的研究不一定能推广到整个系统。
这种研究很重要,因为抗微生物药物是一种珍贵而有限的资源;我们必须减少它们在农业中的不当使用,正如我们必须减少它们在人类医学中的不当使用一样。然而,我们还必须对减少农业中抗微生物药物使用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发生的时间范围有现实的预期。如果大多数后果严重的人类-动物AMR传播是缓慢和间接的,那么现在实施的控制可能需要几年或几十年才能在人类疾病中取得成果(尽管这不是不尝试的理由)。研究这些传播途径也可以帮助我们设计干预和预防这种传播的策略。了解人类-动物AMR传播的适当背景和后果最终应该提醒我们,人类医学中的抗微生物药物管理是重要的,并且可能对人类疾病中的AMR产生更大的短期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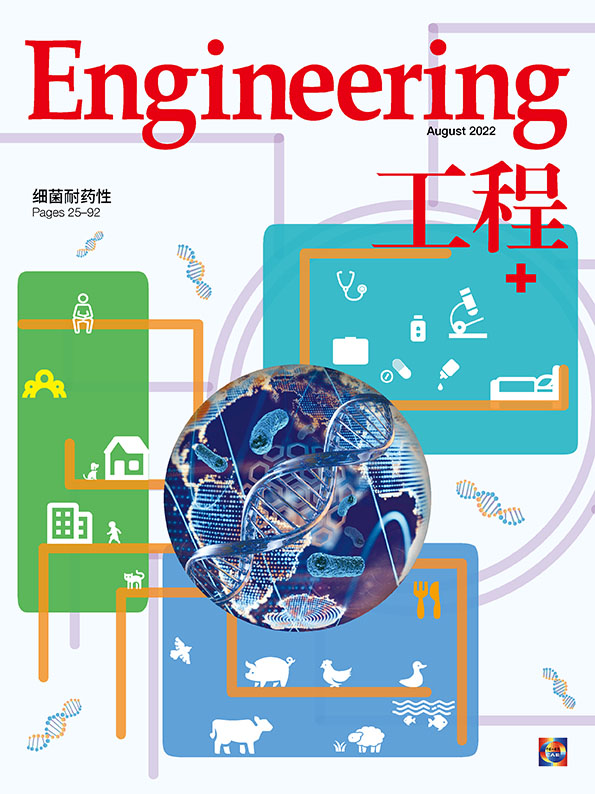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51620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5162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