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 1 ]
Gatti RA, Meuwissen HJ, Allen HD, Hong R, Good RA. Immunological reconstitution of sex-linked lymphopenic immunological deficiency. Lancet 1968;292(7583):1366–9.
链接1
[ 2 ]
Gratwohl A, Pasquini MC, Aljurf M, Atsuta Y, Baldomero H, Foeken L, et al. One million haemopoietic stem-cell transplants: a ret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Lancet Haematol 2015;2(3):e91–100.
链接1
[ 3 ]
Zeiser R, Blazar BR. Acute graft-versus-host disease—biologic process, prevention, and therapy. N Engl J Med 2017;377(22):2167–79.
链接1
[ 4 ]
Barnes DW, Loutit JF. The radiation recovery factor: preservation by the Polge–Smith–Parkes technique. J Natl Cancer Inst 1955;15(4):901–5.
链接1
[ 5 ]
Billingham RE. The biology of graft-versus-host reactions. Harvey Lect 1966– 1967;62:21–78.
链接1
[ 6 ]
Blazar BR, Korngold R, Vallera DA. Recent advances in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GVHD) prevention. Immunol Rev 1997;157(1):79–109.
链接1
[ 7 ]
Tutschka PJ, Beschorner WE, Hess AD, Santos GW. Cyclosporin-A to prevent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a pilot study in 22 patients receiving allogeneic marrow transplants. Blood 1983;61(2):318–25.
链接1
[ 8 ]
Fay JW, Wingard JR, Antin JH, Collins RH, Piñeiro LA, Blazar BR, et al. FK506 (tacrolimus) monotherapy for prevention of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after histocompatible sibling allogenic 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 Blood 1996;87(8):3514–9.
链接1
[ 9 ]
Cutler C, Antin JH. Sirolimus immunosuppression for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prophylaxis and therapy: an update. Curr Opin Hematol 2010;17 (6):500–4.
链接1
[10]
Luznik L, Bolaños-Meade J, Zahurak M, Chen AR, Smith BD, Brodsky R, et al. High-dose cyclophosphamide as single-agent, short-course prophylaxis of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Blood 2010;115(16):3224–30.
链接1
[11]
Luznik L, Jones RJ, Fuchs EJ. High-dose cyclophosphamide for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prevention. Curr Opin Hematol 2010;17(6):493–9.
链接1
[12]
Luznik L, O’Donnell PV, Fuchs EJ. Post-transplantation cyclophosphamide for tolerance induction in HLA-haploidentical 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 Semin Oncol 2012;39(6):683–93.
链接1
[13]
Kanakry CG, Tsai HL, Bolaños-Meade J, Smith BD, Gojo I, Kanakry JA, et al. Single-agent GVHD prophylaxis with posttransplantation cyclophosphamide after myeloablative, HLA-matched BMT for AML, ALL, and MDS. Blood 2014;124(25):3817–27.
链接1
[14]
Ildstad ST, Sachs DH. Reconstitution with syngeneic plus allogeneic or xenogeneic bone marrow leads to specific acceptance of allografts or xenografts. Nature 1984;307(5947):168–70.
链接1
[15]
Sykes M, Sheard M, Sachs DH. Effects of T cell depletion in radiation bone marrow chimeras. I. Evidence for a donor cell population which increases allogeneic chimerism but which lacks the potential to produce GVHD. J Immunol 1988;141(7):2282–8.
链接1
[16]
Bacchetta R, Bigler M, Touraine JL, Parkman R, Tovo PA, Abrams J, et al. High levels of interleukin 10 production in vivo are associated with tolerance in SCID patients transplanted with HLA mismatched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J Exp Med 1994;179(2):493–502.
链接1
[17]
Roncarolo MG, Gregori S, Bacchetta R, Battaglia M. Tr1 cells and the counterregulation of immunity: natural mechanisms and therapeutic applications. Curr Top Microbiol Immunol 2014;380:39–68.
链接1
[18]
Kohrt HE, Turnbull BB, Heydari K, Shizuru JA, Laport GG, Miklos DB, et al. TLI and ATG conditioning with low risk of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retains antitumor reactions after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cell transplantation from related and unrelated donors. Blood 2009;114(5):1099–109.
链接1
[19]
Schneidawind D, Pierini A, Negrin RS. Regulatory T cells and natural killer T cells for modulation of GVHD following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cell transplantation. Blood 2013;122(18):3116–21.
链接1
[20]
Arpaia N, Green JA, Moltedo B, Arvey A, Hemmers S, Yuan S, et al. A distinct function of regulatory T cells in tissue protection. Cell 2015;162(5):1078–89.
链接1
[21]
Fibbe WE, Rabelink TJ. Lupus nephritis: mesenchymal stromal cells in lupus nephritis. Nat Rev Nephrol 2017;13(8):452–3.
链接1
[22]
Shevach EM. Mechanisms of FOXP3+ T regulatory cell-mediated suppression. Immunity 2009;30(5):636–45.
链接1
[23]
Sakaguchi S, Miyara M, Costantino CM, Hafler DA. FOXP3+ regulatory T cells in the human immune system. Nat Rev Immunol 2010;10(7):490–500.
链接1
[24]
Bluestone JA, Tang Q, Sedwick CE. T regulatory cells in autoimmune diabetes: past challenges, future prospects. J Clin Immunol 2008;28(6):677–84.
链接1
[25]
Curotto de Lafaille MA, Lafaille JJ. Natural and adaptive FOXP3+ regulatory T cells: more of the same or a division of labor? Immunity 2009;30(5):626–35.
链接1
[26]
Taylor PA, Noelle RJ, Blazar BR. CD4+ CD25+ immune regulatory cells are required for induction of tolerance to alloantigen via costimulatory blockade. J Exp Med 2001;193(11):1311–8.
链接1
[27]
Schmidt A, Oberle N, Krammer PH.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Treg-mediated T cell suppression. Front Immunol 2012;3:51.
链接1
[28]
McNally A, Hill GR, Sparwasser T, Thomas R, Steptoe RJ. CD4+ CD25+ regulatory T cells control CD8+ T-cell effector differentiation by modulating IL-2 homeostasis.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11;108(18):7529–34.
链接1
[29]
Taylor PA, Lees CJ, Blazar BR. The infusion of ex vivo activated and expanded CD4+ CD25+ immune regulatory cells inhibits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lethality. Blood 2002;99(10):3493–9.
链接1
[30]
Hoffmann P, Ermann J, Edinger M, Fathman CG, Strober S. Donor-type CD4+ CD25+ regulatory T cells suppress lethal acute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after allogeneic 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 J Exp Med 2002;196 (3):389–99.
链接1
[31]
Cohen JL, Trenado A, Vasey D, Klatzmann D, Salomon BL. CD4+ CD25+ immunoregulatory T cells: new therapeutics for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J Exp Med 2002;196(3):401–6.
链接1
[32]
Godfrey WR, Ge YG, Spoden DJ, Levine BL, June CH, Blazar BR, et al. In vitroexpanded human CD4+ CD25+ T-regulatory cells can markedly inhibit allogeneic dendritic cell-stimulated MLR cultures. Blood 2004;104 (2):453–61.
链接1
[33]
Hippen KL, Harker-Murray P, Porter SB, Merkel SC, Londer A, Taylor DK, et al. Umbilical cord blood regulatory T-cell expansion and functional effects of tumor necrosis factor receptor family members OX40 and 4-1BB expressed on artificial antigen-presenting cells. Blood 2008;112(7):2847–57.
链接1
[34]
Godfrey WR, Spoden DJ, Ge YG, Baker SR, Liu B, Levine BL, et al. Cord blood CD4+ CD25+ -derived T regulatory cell lines express FOXP3 protein and manifest potent suppressor function. Blood 2005;105(2):750–8.
链接1
[35]
Trzonkowski P, Bieniaszewska M, Jus´cin´ ska J, Dobyszuk A, Krzystyniak A, Marek N, et al. First-in-man clinical results of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 with human ex vivo expanded CD4+ CD25+ CD127 T regulatory cells. Clin Immunol 2009;133(1):22–6.
链接1
[36]
Brunstein CG, Miller JS, Cao Q, McKenna DH, Hippen KL, Curtsinger J, et al. Infusion of ex vivo expanded T regulatory cells in adults transplanted with umbilical cord blood: safety profile and detection kinetics. Blood 2011;117 (3):1061–70.
链接1
[37]
Brunstein CG, Miller JS, McKenna DH, Hippen KL, DeFor TE, Sumstad D, et al. Umbilical cord blood-derived T regulatory cells to prevent GVHD: kinetics, toxicity profile, and clinical effect. Blood 2016;127(8):1044–51.
链接1
[38]
Di Ianni M, Falzetti F, Carotti A, Terenzi A, Castellino F, Bonifacio E, et al. Tregs prevent GVHD and promote immune reconstitution in HLA-haploidentical transplantation. Blood 2011;117(14):3921–8.
链接1
[39]
Martelli MF, Di Ianni M, Ruggeri L, Falzetti F, Carotti A, Terenzi A, et al. HLAhaploidentical transplantation with regulatory and conventional T-cell adoptive immunotherapy prevents acute leukemia relapse. Blood 2014;124 (4):638–44.
链接1
[40]
Sockolosky JT, Trotta E, Parisi G, Picton L, Su LL, Le AC, et al. Selective targeting of engineered T cells using orthogonal IL-2 cytokine-receptor complexes. Science 2018;359(6379):1037–42.
链接1
[41]
Trotta E, Bessette PH, Silveria SL, Ely LK, Jude KM, Le DT, et al. A human antiIL-2 antibody that potentiates regulatory T cells by a structure-based mechanism. Nat Med 2018;24(7):1005–14.
链接1
[42]
Chopra M, Biehl M, Steinfatt T, Brandl A, Kums J, Amich J, et al. Exogenous TNFR2 activation protects from acute GVHD via host Treg cell expansion. J Exp Med 2016;213(9):1881–900.
链接1
[43]
Chen X, Das R, Komorowski R, Beres A, Hessner MJ, Mihara M, et al. Blockade of interleukin-6 signaling augments regulatory T-cell reconstitution and attenuates the severity of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Blood 2009;114 (4):891–900.
链接1
[44]
Kennedy GA, Varelias A, Vuckovic S, Le Texier L, Gartlan KH, Zhang P, et al. Addition of interleukin-6 inhibition with tocilizumab to standard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prophylaxis after allogeneic stem-cell transplantation: a phase 1/2 trial. Lancet Oncol 2014;15(13):1451–9.
链接1
[45]
Zhang P, Tey SK, Koyama M, Kuns RD, Olver SD, Lineburg KE, et al. Induced regulatory T cells promote tolerance when stabilized by rapamycin and IL-2 in vivo. J Immunol 2013;191(10):5291–303.
链接1
[46]
Robb RJ, Lineburg KE, Kuns RD, Wilson YA, Raffelt NC, Olver SD, et al. Identification and expansion of highly suppressive CD8+ FOXP3+ regulatory T cells after experimental allogeneic 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 Blood 2012;119(24):5898–908.
链接1
[47]
Beres AJ, Haribhai D, Chadwick AC, Gonyo PJ, Williams CB, Drobyski WR. CD8+ FOXP3+ regulatory T cells are induced during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and mitigate disease severity. J Immunol 2012;189(1):464–74.
链接1
[48]
Selvaraj RK, Geiger TL. Mitigation of experimental allergic encephalomyelitis by TGF-b induced FOXP3+ regulatory T lymphocytes through the induction of anergy and infectious tolerance. J Immunol 2008;180(5):2830–8.
链接1
[49]
Godebu E, Summers-Torres D, Lin MM, Baaten BJ, Bradley LM. Polyclonal adaptive regulatory CD4 cells that can reverse type I diabetes become oligoclonal long-term protective memory cells. J Immunol 2008;181 (3):1798–805.
链接1
[50]
Kang SG, Lim HW, Andrisani OM, Broxmeyer HE, Kim CH. Vitamin A metabolites induce gut-homing FOXP3+ regulatory T cells. J Immunol 2007;179(6):3724–33.
链接1
[51]
Golovina TN, Mikheeva T, Brusko TM, Blazar BR, Bluestone JA, Riley JL. Retinoic acid and rapamycin differentially affect and synergistically promote the ex vivo expansion of natural human T regulatory cells. PLoS ONE 2011;6 (1):e15868.
链接1
[52]
Mold JE, Michaëlsson J, Burt TD, Muench MO, Beckerman KP, Busch MP, et al. Maternal alloantigen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olerogenic fetal regulatory T cells in utero. Science 2008;322(5907):1562–5.
链接1
[53]
Tran DQ, Ramsey H, Shevach EM. Induction of FOXP3 expression in naive human CD4+ FOXP3 T cells by T-cell receptor stimulation is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b dependent but does not confer a regulatory phenotype. Blood 2007;110(8):2983–90.
链接1
[54]
Lu L, Zhou X, Wang J, Zheng SG, Horwitz DA. Characterization of protective human CD4+ CD25+ FOXP3+ regulatory T cells generated with IL-2, TGF-b and retinoic acid. PLoS ONE 2010;5(12):e15150.
链接1
[55]
Hippen KL, Merkel SC, Schirm DK, Sieben CM, Sumstad D, Kadidlo DM, et al. Massive ex vivo expansion of human natural regulatory T cells (Tregs) with minimal loss of in vivo functional activity. Sci Transl Med 2011;3 (83):83ra41.
链接1
[56]
Hippen KL, O’Connor RS, Lemire AM, Saha A, Hanse EA, Tennis NC, et al. In vitro induction of human regulatory T cells using conditions of low tryptophan plus kynurenines. Am J Transplant 2017;17(12):3098–113.
链接1
[57]
Bailey-Bucktrout SL, Bluestone JA. Regulatory T cells: stability revisited. Trends Immunol 2011;32(7):301–6.
链接1
[58]
Zhou X, Bailey-Bucktrout S, Jeker LT, Bluestone JA. Plasticity of CD4+ FOXP3+ T cells. Curr Opin Immunol 2009;21(3):281–5.
链接1
[59]
Komatsu N, Okamoto K, Sawa S, Nakashima T, Oh-hora M, Kodama T, et al. Pathogenic conversion of FOXP3+ T cells into Th17 cells in autoimmune arthritis. Nat Med 2014;20(1):62–8.
链接1
[60]
Hua J, Inomata T, Chen Y, Foulsham W, Stevenson W, Shiang T, et al. Pathological conversion of regulatory T cells is associated with loss of allotolerance. Sci Rep 2018;8(1):7059.
链接1
[61]
McClymont SA, Putnam AL, Lee MR, Esensten JH, Liu W, Hulme MA, et al. Plasticity of human regulatory T cells in healthy subjects and patients with type 1 diabetes. J Immunol 2011;186(7):3918–26.
链接1
[62]
Gagliani N, Magnani CF, Huber S, Gianolini ME, Pala M, Licona-Limon P, et al. Coexpression of CD49b and LAG-3 identifies human and mouse T regulatory type 1 cells. Nat Med 2013;19(6):739–46.
链接1
[63]
Gregori S, Roncarolo MG. Engineered T regulatory type 1 cells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Front Immunol 2018;9:233.
链接1
[64]
Zhang P, Lee JS, Gartlan KH, Schuster IS, Comerford I, Varelias A, et al. Eomesodermin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ype 1 regulatory T (TR1) cells. Sci Immunol 2017;2(10):eaah7152.
链接1
[65]
Bacchetta R, Lucarelli B, Sartirana C, Gregori S, Lupo Stanghellini MT, Miqueu P, et al. Immunological outcome in haploidentical-HSC transplanted patients treated with IL-10-anergized donor T cells. Front Immunol 2014;5:16.
链接1
[66]
Jiang Y, Vaessen B, Lenvik T, Blackstad M, Reyes M, Verfaillie CM. Multipotent progenitor cells can be isolated from postnatal murine bone marrow, muscle, and brain. Exp Hematol 2002;30(8):896–904.
链接1
[67]
Prockop DJ. Marrow stromal cells as stem cells for nonhematopoietic tissues. Science 1997;276(5309):71–4.
链接1
[68]
Pittenger MF, Mackay AM, Beck SC, Jaiswal RK, Douglas R, Mosca JD, et al. Multilineage potential of adult human mesenchymal stem cells. Science 1999;284(5411):143–7.
链接1
[69]
Dominici M, Le Blanc K, Mueller I, Slaper-Cortenbach I, Marini F, Krause D, et al. Minimal criteria for defining multipotent mesenchymal stromal cells.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ellular therapy position statement. Cytotherapy 2006;8(4):315–7.
链接1
[70]
Covas DT, Panepucci RA, Fontes AM, Silva WA Jr, Orellana MD, Freitas MC, et al. Multipotent mesenchymal stromal cells obtained from diverse human tissues share functional properties and gene-expression profile with CD146+ perivascular cells and fibroblasts. Exp Hematol 2008;36(5):642–54.
链接1
[71]
Auletta JJ, Eid SK, Wuttisarnwattana P, Silva I, Metheny L, Keller MD, et al. Human mesenchymal stromal cells attenuate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and maintain graft-versus-leukemia activity following experimental allogeneic 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 Stem Cells 2015;33(2):601–14.
链接1
[72]
Meisel R, Zibert A, Laryea M, Göbel U, Däubener W, Dilloo D. Human bone marrow stromal cells inhibit allogeneic T-cell responses by indoleamine 2,3- dioxygenase-mediated tryptophan degradation. Blood 2004;103 (12):4619–21.
链接1
[73]
Duffy MM, Pindjakova J, Hanley SA, McCarthy C, Weidhofer GA, Sweeney EM, et al. Mesenchymal stem cell inhibition of T-helper 17 cell-differentiation is triggered by cell–cell contact and mediated by prostaglandin E2 via the EP4 receptor. Eur J Immunol 2011;41(10):2840–51.
链接1
[74]
Qu X, Liu X, Cheng K, Yang R, Zhao RC.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nhibit Th17 cell differentiation by IL-10 secretion. Exp Hematol 2012;40(9):761–70.
链接1
[75]
Highfill SL, Kelly RM, O’Shaughnessy MJ, Zhou Q, Xia L, Panoskaltsis-Mortari A, et al. Multipotent adult progenitor cells can suppress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via prostaglandin E2 synthesis and only if localized to sites of allopriming. Blood 2009;114(3):693–701.
链接1
[76]
Wang D, Yu Y, Haarberg K, Fu J, Kaosaard K, Nagaraj S, et al. Dynamic change and impact of 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 in allogeneic 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 in mice. Biol Blood Marrow Transplant 2013;19(5):692–702.
链接1
[77]
Ren G, Zhang L, Zhao X, Xu G, Zhang Y, Roberts AI, et al. Mesenchymal stem cell-mediated immunosuppression occurs via concerted action of chemokines and nitric oxide. Cell Stem Cell 2008;2(2):141–50.
链接1
[78]
Tipnis S, Viswanathan C, Majumdar AS. Immunosuppressive properties of human umbilical cord-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role of B7-H1 and IDO. Immunol Cell Biol 2010;88(8):795–806.
链接1
[79]
Davies LC, Heldring N, Kadri N, Le Blanc K. Mesenchymal stromal cell secretion of programmed death-1 ligands regulates T cell mediated immunosuppression. Stem Cells 2017;35(3):766–76.
链接1
[80]
Lim JY, Ryu DB, Lee SE, Park G, Min CK. Mesenchymal stem cells (MSCs) attenuate cutaneous sclerodermatous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Scl-GVHD) through inhibition of immune cell infiltration in a mouse model. J Invest Dermatol 2017;137(9):1895–904.
链接1
[81]
Phinney DG, Pittenger MF. Concise review: MSC-derived exosomes for cellfree therapy. Stem Cells 2017;35(4):851–8.
链接1
[82]
Di Trapani M, Bassi G, Midolo M, Gatti A, Kamga PT, Cassaro A, et al. Differential and transferable modulatory effects of mesenchymal stromal cell-derived extracellular vesicles on T, B and NK cell functions. Sci Rep 2016;6(1):24120.
链接1
[83]
Mokarizadeh A, Delirezh N, Morshedi A, Mosayebi G, Farshid AA, Mardani K. Microvesicles derived from mesenchymal stem cells: potent organelles for induction of tolerogenic signaling. Immunol Lett 2012;147(1–2):47–54.
链接1
[84]
Amarnath S, Foley JE, Farthing DE, Gress RE, Laurence A, Eckhaus MA, et al. Bone marrow-derived mesenchymal stromal cells harness purinergenic signaling to tolerize human Th1 cells in vivo. Stem Cells 2015;33(4):1200–12.
链接1
[85]
Ragni E, Banfi F, Barilani M, Cherubini A, Parazzi V, Larghi P, et al. Extracellular vesicle-shuttled mRNA in mesenchymal stem cell communication. Stem Cells 2017;35(4):1093–105.
链接1
[86]
Galleu A, Riffo-Vasquez Y, Trento C, Lomas C, Dolcetti L, Cheung TS, et al. Apoptosis in mesenchymal stromal cells induces in vivo recipient-mediated immunomodulation. Sci Transl Med 2017;9(416):eaam7828.
链接1
[87]
Alfaro MP, Deskins DL, Wallus M, DasGupta J, Davidson JM, Nanney LB, et al. A physiological role for connective tissue growth factor in early wound healing. Lab Invest 2013;93(1):81–95.
链接1
[88]
Chen L, Tredget EE, Wu PY, Wu Y. Paracrine factors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s recruit macrophages and endothelial lineage cells and enhance wound healing. PLoS ONE 2008;3(4):e1886.
链接1
[89]
Reiter J, Drummond S, Sammour I, Huang J, Florea V, Dornas P, et al. Stromal derived factor-1 mediates the lung regenerative effects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n a rodent model of 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 Respir Res 2017;18 (1):137.
链接1
[90]
Le Blanc K, Rasmusson I, Sundberg B, Götherström C, Hassan M, Uzunel M, et al. Treatment of severe acute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with third party haploidentical mesenchymal stem cells. Lancet 2004;363(9419):1439–41.
链接1
[91]
Ringdén O, Uzunel M, Rasmusson I, Remberger M, Sundberg B, Lönnies H, et al. Mesenchymal stem cells for treatment of therapy-resistant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Transplantation 2006;81(10):1390–7.
链接1
[92]
Fang B, Song Y, Liao L, Zhang Y, Zhao RC. Favorable response to human adipose tissue-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n steroid-refractory acute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Transplant Proc 2007;39(10):3358–62.
链接1
[93]
Le Blanc K, Frassoni F, Ball L, Locatelli F, Roelofs H, Lewis I, et al. Mesenchymal stem cells for treatment of steroid-resistant, severe, acute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a phase II study. Lancet 2008;371(9624):1579–86.
链接1
[94]
Von Bonin M, Stölzel F, Goedecke A, Richter K, Wuschek N, Hölig K, et al. Treatment of refractory acute GVHD with third-party MSC expanded in platelet lysate-containing medium. Bone Marrow Transplant 2009;43 (3):245–51.
链接1
[95]
Kebriaei P, Isola L, Bahceci E, Holland K, Rowley S, McGuirk J, et al. Adult human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dded to corticosteroid therapy for the treatment of acute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Biol Blood Marrow Transplant 2009;15(7):804–11.
链接1
[96]
Pérez-Simon JA, López-Villar O, Andreu EJ, Rifón J, Muntion S, Campelo MD, et al. Mesenchymal stem cells expanded in vitro with human serum for the treatment of acute and chronic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results of a phase I/ II clinical trial. Haematologica 2011;96(7):1072–6.
链接1
[97]
Herrmann R, Sturm M, Shaw K, Purtill D, Cooney J, Wright M, et al. Mesenchymal stromal cell therapy for steroid-refractory acute and chronic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 a phase 1 study. Int J Hematol 2012;95(2):182–8.
链接1
[98]
Muroi K, Miyamura K, Ohashi K, Murata M, Eto T, Kobayashi N, et al. Unrelated allogeneic bone marrow-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for steroid-refractory acute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a phase I/II study. Int J Hematol 2013;98(2):206–13.
链接1
[99]
Kurtzberg J, Prockop S, Teira P, Bittencourt H, Lewis V, Chan KW, et al. Allogeneic human mesenchymal stem cell therapy (remestemcel-L, Prochymal) as a rescue agent for severe refractory acute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in pediatric patients. Biol Blood Marrow Transplant 2014;20 (2):229–35.
链接1
[100]
Hashmi S, Ahmed M, Murad MH, Litzow MR, Adams RH, Ball LM, et al. Survival after mesenchymal stromal cell therapy in steroid-refractory acute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Lancet Haematol 2016;3(1):e45–52.
链接1
[101]
Ball LM, Bernardo ME, Roelofs H, Lankester A, Cometa A, Egeler RM, et al. Cotransplantation of ex vivo expand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ccelerates lymphocyte recovery and may reduce the risk of graft failure in haploidentical hematopoietic stem-cell transplantation. Blood 2007;110 (7):2764–7.
链接1
[102]
Bernardo ME, Ball LM, Cometa AM, Roelofs H, Zecca M, Avanzini MA, et al. Coinfusion of ex vivo-expanded, parental MSCs prevents life-threatening acute GVHD, but does not reduce the risk of graft failure in pediatric patients undergoing allogeneic umbilical cord blood transplantation. Bone Marrow Transplant 2011;46(2):200–7.
链接1
[103]
MacMillan ML, Blazar BR, DeFor TE, Wagner JE. Transplantation of ex-vivo culture-expanded parental haploidentical mesenchymal stem cells to promote engraftment in pediatric recipients of unrelated donor umbilical cord blood: results of a phase I-II clinical trial. Bone Marrow Transplant 2009;43(6):447–54.
链接1
[104]
Reyes M, Dudek A, Jahagirdar B, Koodie L, Marker PH, Verfaillie CM. Origin of endothelial progenitors in human postnatal bone marrow. J Clin Invest 2002;109(3):337–46.
链接1
[105]
Schwartz RE, Reyes M, Koodie L, Jiang Y, Blackstad M, Lund T, et al. Multipotent adult progenitor cells from bone marrow differentiate into functional hepatocyte-like cells. J Clin Invest 2002;109(10):1291–302.
链接1
[106]
Boozer S, Lehman N, Lakshmipathy U, Love B, Raber A, Maitra A, et al. Global characterization and genomic stability of human multistem, a multipotent adult progenitor cell. J Stem Cells 2009;4(1):17–28.
链接1
[107]
Jacobs SA, Pinxteren J, Roobrouck VD, Luyckx A, van’t Hof W, Deans R, et al. Human multipotent adult progenitor cells are nonimmunogenic and exert potent immunomodulatory effects on alloreactive T-cell responses. Cell Transplant 2013;22(10):1915–28.
链接1
[108]
Reading JL, Vaes B, Hull C, Sabbah S, Hayday T, Wang NS, et al. Suppression of IL-7-dependent effector T-cell expansion by multipotent adult progenitor cells and PGE2. Mol Ther 2015;23(11):1783–93.
链接1
[109]
Kovacsovics-Bankowski M, Streeter PR, Mauch KA, Frey MR, Raber A, van’t Hof W, et al. Clinical scale expanded adult pluripotent stem cells prevent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Cell Immunol 2009;255(1–2):55–60.
链接1
[110]
Maziarz RT, Devos T, Bachier CR, Goldstein SC, Leis JF, Devine SM, et al. Single and multiple dose MultiStem (multipotent adult progenitor cell) therapy prophylaxis of acute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in myeloablative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cell transplantation: a phase 1 trial. Biol Blood Marrow Transplant 2015;21(4):720–8.
链接1
[111]
Riley JL, June CH, Blazar BR. Human T regulatory cell therapy: take a billion or so and call me in the morning. Immunity 2009;30(5):656–65.
链接1
[112]
McKenna DH Jr, Sumstad D, Kadidlo DM, Batdorf B, Lord CJ, Merkel SC, et al. Optimization of cGMP purification and expansion of umbilical cord blood-derived T-regulatory cells in support of first-in-human clinical trials. Cytotherapy 2017;19(2):250–62.
链接1
[113]
Tolar J, Nauta AJ, Osborn MJ, Panoskaltsis Mortari A, McElmurry RT, Bell S, et al. Sarcoma derived from cultur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Stem Cells 2007;25(2):371–9.
链接1
[114]
Blazar BR, MacDonald KPA, Hill GR. Immune regulatory cell infusion for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prevention and therapy. Blood 2018;131(24):2651–60.
链接1
[115]
Agle K, Vincent BG, Piper C, Belle L, Zhou V, Shlomchik W, et al. Bim regulates the survival and suppressive capability of CD8+ FOXP3+ regulatory T cells during murine GVHD. Blood 2018;132(4):435–47.
链接1
[116]
Belle L, Agle K, Zhou V, Yin-Yuan C, Komorowski R, Eastwood D, et al. Blockade of interleukin-27 signaling reduces GVHD in mice by augmenting Treg reconstitution and stabilizing FOXP3 expression. Blood 2016;128 (16):2068–82.
链接1
[117]
Heinrichs J, Li J, Nguyen H, Wu Y, Bastian D, Daethanasanmak A, et al. CD8+ Tregs promote GVHD prevention and overcome the impaired GVL effect mediated by CD4+ Tregs in mice. OncoImmunology 2016;5(6):e1146842.
链接1
[118]
Highfill SL, Rodriguez PC, Zhou Q, Goetz CA, Koehn BH, Veenstra R, et al. Bone marrow 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 (MDSCs) inhibit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GVHD) via an arginase-1-dependent mechanism that is up-regulated by interleukin-13. Blood 2010;116(25):5738–47.
链接1
[119]
Koehn BH, Apostolova P, Haverkamp JM, Miller JS, McCullar V, Tolar J, et al. GVHD-associated, inflammasome-mediated loss of function in adoptively transferred 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 Blood 2015;126(13):1621–8.
链接1
[120]
Zhou Z, French DL, Ma G, Eisenstein S, Chen Y, Divino CM, et al.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 of 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 generated from mouse embryonic and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Stem Cells 2010;28(3):620–32.
链接1
[121]
Leveson-Gower DB, Olson JA, Sega EI, Luong RH, Baker J, Zeiser R, et al. Low doses of natural killer T cells provide protection from acute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via an IL-4-dependent mechanism. Blood 2011;117(11):3220–9.
链接1
[122]
Schneidawind D, Baker J, Pierini A, Buechele C, Luong RH, Meyer EH, et al. Third-party CD4+ invariant natural killer T cells protect from murine GVHD lethality. Blood 2015;125(22):3491–500.
链接1
[123]
Du J, Paz K, Thangavelu G, Schneidawind D, Baker J, Flynn R, et al. Invariant natural killer T cells ameliorate murine chronic GVHD by expanding donor regulatory T cells. Blood 2017;129(23):3121–5.
链接1
[124]
Bruce DW, Stefanski HE, Vincent BG, Dant TA, Reisdorf S, Bommiasamy H, et al. Type 2 innate lymphoid cells treat and prevent acute gastrointestinal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J Clin Invest 2017;127(5):1813–25.
链接1
[125]
Sato K, Yamashita N, Baba M, Matsuyama T. Modified myeloid dendritic cells act as regulatory dendritic cells to induce anergic and regulatory T cells. Blood 2003;101(9):3581–9.
链接1
[126]
Sato K, Yamashita N, Yamashita N, Baba M, Matsuyama T. Regulatory dendritic cells protect mice from murine acute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and leukemia relapse. Immunity 2003;18(3):367–79.
链接1
[127]
MacDonald KP, Rowe V, Clouston AD, Welply JK, Kuns RD, Ferrara JL, et al. Cytokine expanded myeloid precursors function as regulatory antigenpresenting cells and promote tolerance through IL-10-producing regulatory T cells. J Immunol 2005;174(4):1841–50.
链接1
[128]
Yang J, Li R, Ren Y, Yang Y, Xie R, Fan H. Third-party tolerogenic dendritic cells reduce allo-reactivity in vitro and ameliorate the severity of acute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in allo-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 Scand J Immunol 2013;78(6):486–96.
链接1
[129]
D’Aveni M, Rossignol J, Coman T, Sivakumaran S, Henderson S, Manzo T, et al. G-CSF mobilizes CD34+ regulatory monocytes that inhibit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Sci Transl Med 2015;7(281):281ra42.
链接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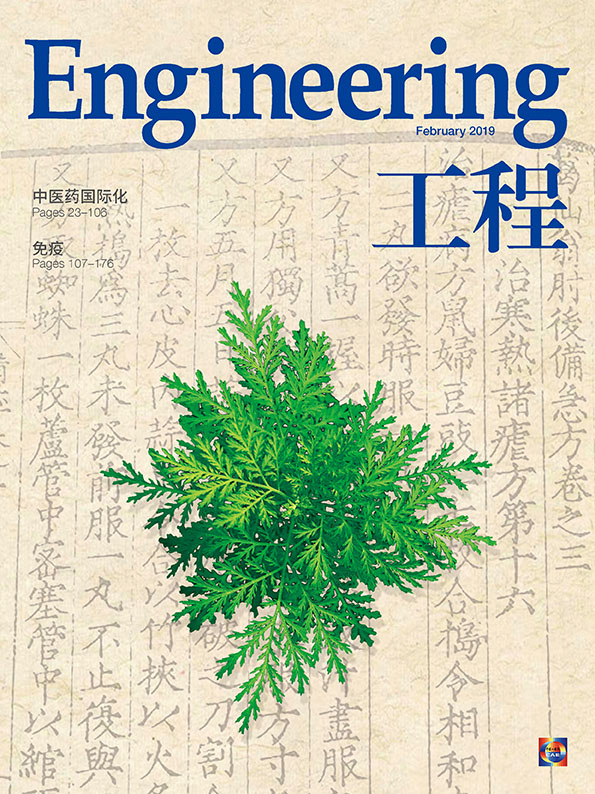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51620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51620号




